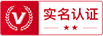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维护世界语言多样性及平衡性的探讨文献综述
2020-04-21 16:23:11
一、研究的背景、目的及意义
1.研究的背景
在英语日益成为世界语言且语言多样性逐渐衰退的环境下,人们开始思考如何保护濒危语言甚至使已经灭亡的语言重获新生。语言多样性的锐减可以追溯到15~19世纪的欧洲殖民扩张,除了殖民地的动植物外,欧洲殖民者还在当地发现了他们此前从未想象到的精神世界。殖民地的语言用“全新”的概念呈现出了人类的经验与想法,殖民者当时还无法理解自身掌握的语言和殖民地语言的区别。伴随着在殖民地资本的积累、土地的抢占,为了更好地“管理”殖民地,欧洲殖民者也悄然开启了文化入侵。在原住民被雇佣作为劳工时,他们不得不遗弃自己的母语转而使用更为强势的语言。让情况更加恶化的是破坏语言成功代际传递的诸多因素:当地儿童迫于社会压力,意识到自己母语的不利地位而选择使用强势语言时,这种本土语言的消亡趋势不可逆转,英语中该现象被称为moribund(Harrison, 2007)。例如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北昆士兰州,原本一共有6个讲着一种澳大利亚土著语言——迪尔巴尔语(Dyirbal)的聚落栖息于这片水草肥美的区域,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1864年英国殖民者扩张至该区域,除了破坏了森林植被,也改变了当地部落的文化习俗,原住民对迪尔巴尔语使用的变化最为明显。
在2001年,全世界至少使用着6912种自然语言。如今众多语言学家推测截止到21世纪末——2101年,仅有一半的语言会仍被使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预测,截止到本世纪末,6000种语言的50%~90%会被强势语言所替代。甚至在今天,就存在某种语言仅有10人使用的现象。根据当前语言消失的速度,我们大约每十天就会失去一种语言,纵览全球,这种消失仍在加速。语言学家Ken Hale曾把语言消亡比喻为在卢浮宫投掷一枚炸弹:“每当我们失去一种语言,我们也就失去了一种文化,一种智慧财富,甚至是一件艺术品。”据可靠估计,世界上87%的动植物没有被当代科学识别、命名、描述与分类,这其中还并未包括无法被肉眼看到的微生物。我们在失去一种语言时失去的远不止这些动植物,还包括被记录在在土著语言中很难被更加强势的世界语言所表达的传统知识,比如月相、风型、西伯利亚原住民用自己的语言记录下的驯鹿的分类方法……当一种语言消失时,长期形成的、导向人与自然互动的知识也会消失。语言消失的其他后果将是文化财富和人类认知的消失。世界上的多数语言从未被科学地记录与描述,我们在失去一种语言时,其连带损失甚至无法估测与计量。
当今世界语言的使用与分布存在着极其明显的不平衡性。世界上共有70亿人口,至少有6912种语言被使用。如果平均分配,那么每一种语言本应该有917000名使用者。但实际上,语言—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让人惊叹。最大的10种语言每一种都有数亿的使用者,占据着总人口的50%。由于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及其殖民主义、20世纪美国在通讯科技领域的创新和全球化进程,世界上有3.5亿人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10亿人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如果我们放眼世界上使用者数量最多的83种语言,那么这83种语言的使用者就占据了总人口的80%。世界上最少被使用的语言大约有3500种,其使用者仅占总人口的0.2%。使用人数少于5000人的语言约占了总语言数量的一半,拥有消亡的潜在风险。此外,全球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会让小语种在拥挤的都市空间内丧失用武之地和存活的机会。在我国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在我国被使用的一半语言中,每一种的使用人数不足万人,仅有千人以内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有20种左右,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然而,约90%的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人口集中在壮语、维吾尔语等15种语言中(杜茜,2011)。
生态语言学是生态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在学术界广为熟知的主要是“豪根模式”(Haugen)和“韩礼德模式”(Halliday)。前者将语言和言语社团、所用语言之社会或所用语言之人对语言的态度之间的关系比作生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言语社团态度的积极与否代表了语言生存环境的良莠。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语言的发展;反之,阻碍语言的发展。因此“豪根式”又被称作“隐喻说”。“韩礼德模式” 将语言的运动与实际的自然生态直接联系起来,因此其被称为“非隐喻说”。国外的生态语言学已有40余年的历史,在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学术组织是2016年成立的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该学会是在2004年Stibbe建立的“语言与生态中心”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生态语言学者们发表出版了大量相关论文、论文集和专著。国内的生态语言学起步较晚,在21世纪初才逐渐广为关注,而且主要以豪根式为主,用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和保护。在生态环境日益陷入危机的今天,运用韩礼德模式分析语言多样性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如今,以黄国文为代表的中国生态语言学学者,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谐”思想,正在积极致力于生态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周文娟,2017)。
2.选题研究目的与意义
(1)目的
基于生态语言学视域,借助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分析世界语言生态失衡的原因,讨论维护世界语言多样性及生态平衡的意义,探讨维护世界语言多样性的措施。进一步讨论语言多样性与世界共同语之间的平衡,在保证世界共同语可以满足不同民族的人进行交流、降低语言经济成本的同时,也积极维护语言特别是濒危的土著语言的多样性。
辩证地看待日益成为一门世界通用语的英语的地位。英语在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中,也衍生出众多变体并且成为当地民族身份的象征,比如新加坡式英语、非洲的克里奥尔语,即使是澳大利亚英语也包含当地的土著词汇(Crystal, 2003)。例如新加坡人只有在自己社群内部才会使用新加坡式英语,因为这代表了他们对社群的认同,在他们和社群外部的人交流时仍会使用具有交际作用的标准英语。有趣的是,标准英语母语者也无法理解这些英语变体,对他们而言无异于一门“外语”。但是其对语言多样性的积极意义和土著语言带来的积极意义存在区别,这种区别也是本文研究的目标之一。
(2)意义
理论层面,本文尝试将豪根与韩礼德两种生态语言学分析模式有机结合进行语言多样性的研究,因此本文意在于探求这两种模式在研究语言多样性时的内在联系。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弱小语言实用性不强,无法给使用者带来经济利益,复兴项目的投资是无效的,但是每一种民族语言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为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蕴涵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语言多样性同生物多样性一样,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应用层面上,本文探讨如何维护语言多样性与平衡性,并根据已有文献提出如何制定出更为合理、健康的语言规划方案,例如语言学家、教育工作者和积极分子首先应在教育体系内鼓励用濒危语言进行授课,支持改进教育政策;在培养读写能力和培训本土语言记录技能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鼓励本土语言文字工作者创制文字符号,培养其读写、分析本土语言的能力;支持并改进更灵活、民主的语言政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土著语言的现代化为维护语言生态平衡提出了参考策略。
二、国内外相关课题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综述
(1)生态语言学
生态语言学的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具有互补关系,语言的跟踪调查和语言政策的制定都要以了解语言的特点及其在言语社团中的地位为前提,而维护语言多样性是维护文化多元化的一部分,有助于我们通过语言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生态问题(赵蕊华、黄国文,201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生物多样性的锐减,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消失都会威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杜茜,2011)。Chawla(2001)以语言学和哲学为基点,认为这两个领域映射了北美印第安人和欧洲殖民者对待自然环境的不同态度。
(2)集中于田野调查
众多外国研究机构、学者都曾致力于多种土著语言的田野调查。有关北美语言的最早记录来自于法国探险家Jacques Cartier等人的单词列表,他们于1534年遇到了居住在当今魁北克城圣劳伦斯河畔的伊洛魁部落。在随后的1539~1543年间,Hernando de Soto,Juan Rodriguez Cabrillo和Martin Frobisher等人都到达了北美洲各地并记录当地语言。直到19世纪,在加利福尼亚州仍有众多鲜为外界所知的部落和语言。人们知道当今在北美洲, 300种独特的、互不相通的语言(mutually unintelligible languages)曾经被使用着,多数的语言已经消失,无迹可寻。虽然这些早期的成果仍有欠缺,例如记录者专业知识的匮乏、在某地考察的时间不够充足,记录手段比较落后等,但是相关工作不断取得进步,理论不断发展。人们认识对语言多样性认识不断深入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很多语言都在快速消失,因此记录工作刻不容缓。1787年Thomas Jefferson号召人们记录北美大陆的词汇,1820年John Pickering发明出音标字母帮助抄写人员更好地处理北美土著语言中不熟悉的语音。抄写惯例不断发展,甚至被纳入到美国民俗学会田野工作者的调查问卷或明细清单中除了语法范例和句子翻译外,还有各个领域的词汇列表。当人们在记录语言的过程中,也认识到了当地原住民的文化与欧洲殖民者的文化大有不同,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学者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语言在文化中的作用。促进北美人类学与语言学形成的最重要人物Franz Boas在哥伦比亚大学告诉他的学生要关注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文本,他和他的学生,特别是Edward Sapir都认为能够区分开语言的最独特特点存在于自然、连贯的言语中,但是这些言语很难被纸和笔记录。直到20世纪中期,录音机、录像机和电脑的发明使得田野调查中言语的记录更为便捷。
众多学者也曾在同样被欧洲殖民者占领的澳大利亚土著语言(aboriginal languages)做过详尽的调查。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Dixon(2002)对澳大利亚土著语言的现状评论道:“就我们所知,从过去到现在澳洲大陆的土著居民一共讲述着240~250种语言,过半数的语言如今已经被人丢弃或遗忘,有20多种语言已经不被儿童学习或者习得了,剩余的语言也仅仅是被中年人或者老年人使用,每十年就有几种澳大利亚土著语言被停止使用或者遗忘。”Dixon(1972)主要对传统的迪尔巴尔语—澳大利亚快速消失语言的典型案例做了详尽的研究,包括使用该语言的部落及其历史文化背景、词语的分类、句法规则、构词法、语音、语义以及澳大利亚各语言间的传播等,Schmidt(1983)在该基础上,进一步对比了被英语影响的新型迪尔巴尔语和传统迪尔巴尔的区别。Lakoff(1987)也提到了当今Dirybal的年轻人被同化后,在新型迪尔巴尔语中的词汇划分与传统迪尔巴尔语的区别。
(2)本体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研究
传统来讲,学者对语言多样性的研究主要采用本体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的方法,但近年来也开始对其进行应用语言学跨学科地研究。Mithun(2004)论述到语言多样性的研究对人类学、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等领域有显著影响。第一,发现语言的基因关系,即解密语言的起源。例如John Wesley Powell发现北美土著语言的词汇有体系化的相似性,在1891年的科研成果Indian Linguistic Families of America North of Mexico中将北美语言分成了50多种。Dixon(1972)也提到澳大利亚的每个部落都说着一种独特的方言,但是多数方言都在词汇和语法上有大量的相似性,因此多数澳大利亚土著语言都属于亲属语言。并且Mithun认为亲属语言的重构可以告诉我们使用者所共享的文化联结。第二,用于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根据语言间的共性划分出语言的主要类型。第三,探求语言、思想、文化与社会间的关系。比如在迪尔巴尔语中,用于描述烹煮当地豌豆的词语特别详尽,这表明这种食物在当地居民饮食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语言虽有共性,但词法和语法差异显著。例如一种语言中的某个单词无法与另一种语言里的单词对应,在北美的Mohawk语中一个简单的单词所表达的意义需要英语中的一个词组或整句才可以表达……这体现出人们认知上的差异。
(3)语言濒危原因的分析
Harrison(2007)指出认为语言的转换或消失往往始于3个因素:殖民,屠杀或同化;城市化;语言歧视。例如,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欧洲殖民者对澳大利亚北昆士兰州的开垦和殖民据点的建立、对原住民的屠杀,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逐渐消失,被欧洲文化所同化。多数人放弃了Dyirbal转而采用英语,孩子们也被禁止在学校中使用Dyirbal(Dixon, 1972)。Muehlmann(2008)的民族志围绕墨西哥北部的本土居民点El Mayor的土著语言Cucapá中的粗话展开了研究。在20世纪早期,该居民点受到歧视并被迫同化到墨西哥社会中,儿童被禁止在学校使用这种语言,墨西哥政府强迫他们使用西班牙语。但如今,意识到保护濒危语言必要性的政府又转变了对Cucapá的态度。讽刺的是,当地人对政府态度的转变并不接受。他们现在对自身的认同并不存在于Cucapá,而在于历史上遭到的不公和当年被政府的漠视中。
(4)语言消失影响的研究
Harrison (2007)、杜茜 (2011)、Ceramella (2012)都强调一种语言的消失意味着一种文化、一个人类知识宝库、一种看待世界的特定视角和认知随之消失。一种语言蕴含着独特的思考方式,反映出内在的自我和使用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还承担着自身认同的功能。如今多数非洲国家仍在使用当年西方殖民时期的语言政策,加之全球化下西方传媒的影响力和现代城市化思维方式随着语言的传播在非洲大地上蔓延,非洲原有的部族文化特色逐渐模糊,出现文化传承、民族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罗美娜,2011)。正如上文所提,很多语言都记录着鲜为人知的动植物(Harrison, 2007; Ceramella, 2012)。生物多样的地区也有多种被使用的语言,语言的消亡也使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崩溃(Ceramella, 2012)。
如今一些学者认为英语已经成为一门世界语言。例如Crystal (2002)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英语发展势头强劲,很难有外界因素阻挡英语成为一门世界通用语言。然而,也有人持相反观点。McArthur (1998)在其著作The English Languages中强调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也产生了诸多英语变体,不同的英语会分化为不同的语言。英语正在经受一种彻底的变化,这种最终会导致英语成为一种语系。Graddol (1998)在The Future of English中分析了影响英语最终角色的诸多当代趋势,认为英语是可以遏制的。通过强调语言使用的内在不可预测性,他认为正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英语浪潮会最终导致英语失去其地位,并且21世纪会出现新的语言分层的可能性。Ceramella(2012)在论文中提到了欧盟内部将会使用的EuroEnglish,这种结果也许让英语付出相应的代价——失去其原本特色。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生态语言学、语言多样性和英语作为一门世界语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些许成果。研究内容的广度和研究触到的深度都很值得肯定,有力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理论发展,并指导现实中对濒危语言的保护、英语作为一门世界语言和其他通用语设置的健康规划。
{title}
2.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案
{title}研究基本内容和技术方案
1. 基本内容
本文使用文献法,通过收集、整理、借鉴等方式,对现有的生态语言学、语言多样性、语言规划和社会语言学等理论、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归纳研究。
另外通过查阅资料和案例分析澳大利亚迪尔巴尔语的变化历程,归纳地总结小语种(minority language)受到威胁的人为因素、发展走向和影响等,并且探讨语言消失对言语社团,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反思欧洲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生态与社会的破坏。
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维护语言多样性与平衡性,并根据已有文献提出如何制定出更为合理、健康的语言规划方案。
2. 研究方案
文献查阅法、案例分析法、语言—文化—历史等多维解释法等。
(1)整理分析前人的研究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2)理论联系实际,确立本文基于澳大利亚北昆士兰州的迪尔巴尔语消亡的案例分析;
(3)运用归纳法,总结语言消亡的因素、过程和结果。
本文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案决定了本文的创新之处,与前人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1)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互为补充地探讨语言多样性和平衡性;
(2)除了对世界语言多样性的论述外,也不忽略世界通用语或世界语言的确立与推进。
(3)从人类发展的历史中寻求适用于我国语言规划的合理方案。
3. 参考文献
[1] The Value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Viewing other Worlds through North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A Compan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llesandro Duranti, ed. Oxford: Blackwell's. 121-140.
[2] Harrison D. When Languages Die: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and the Erosion of Human Knowledge: A World of Many (Fewer) Voices[OL].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January)[ 21 May 2018]. www.oxfordscholarship.com
[3] Dixon, R. M. W. The Dyirbal language of North Queenslan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4] Schmidt, A. Young People’s Dyirbal: An example of language death from Australia[D].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3.
[5] 杜茜. 从生物多样性到语言多样性[J]. 北方语言论丛, 2011(00): 251-262
[6] 赵蕊华,黄国文. 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分析——黄国文教授访谈[J].当代外语研究,2017( 4) : 8-12.
[7] 周文娟. 中国语境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理念与实践——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03): 24-28
[8] Chawla, S. Linguistics and genes, peoples and languages: Linguistic and Philosophical Roots of Our Environmental Crisis [J].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s: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2001, 13 (3): 253-262
[9] Dixon, R. M. W. Australian languages: Their nature and developmen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1] Muehlmann S. “Spread your ass cheeks” And other things that should not be said in indigenous languages [J]. AMERICAN ETHNOLOGIST, 2008, 35, 1:34-48
[12] Ceramella N. Is English a Killer Language or an International Auxiliary? Its Use and Function in a Globalised Worl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08, 1:9-23
[13] 罗美娜. 非洲国家的多元语言使用问题[J]. 世界民族. 2011(02):76-81
[14] Crystal D.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 张廷国,郝树壮. 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6] 黄国文. 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J]. 中国语文,2016(1):1,9-12.
[17] 白瑞斯,王霄冰,刘明. 世界濒危语言的抢救和复兴 —— — 以美国南加州卡维亚语的记录与分析为例[J]. 江西社会科学.2009(3):251-256
[18] 苏·赖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M]. 陈新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9] 范俊军,宫齐,胡鸿雁.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J]. 民族语文. 2006(03):51-61
[20] Nettle D. Explaining Global Patterns of Language Diversity[J].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98, 4:354-374
[21] 何俊芳. 语言人类学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22] Pullum G. The Great Eskimo Vocabulary Hoax[J]. Natural Language amp; Linguistic Theory, 1989, 7(2): 275-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