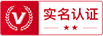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民俗想象外文翻译资料
2022-07-25 13:11:10
Introduction - The literary coteri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media landscape
Looking more closely at the values and mechanisms of scribal culture and publication, Love and Ezell have noted a deep-rooted habit of transcription, a relative informality and frankness of style, a “delight in mixture,” and a general unconcern to distinguish between individual authors contributing to a collection or to attribute works accurately.33 Arthur Marotti, in Manuscript, Print, and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Lyric (1995), has discussed in even greater detail the features of scribal authorship and the productions which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developing medium of print – features such as an open-ended, non-individu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osition process; the socially embedded, or “occasional,” nature of such compositions; a unity created by social context (for example, a place of origin like the Inns of Court) rather than by uniformity of style or skill; and the related prevalence of certain forms, such as answers, imitations, epitaphs, and epigrams, and of potentially offensive subject matter. Paul Trolander and Zeynep Tenger, in Sociable Criticism in England, 1625–1725, have turned their attention more specifically to the literary critical practices of coteries, characterized by a communal, “amendment” approach to the refinement of a work, whereby criticism is an expression of social obligations, and literary activity functions internally to “create and build social bonds,” which in turn serve the group as a whole “by establishing its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restige.”34
This invaluable historical work on the structures and practices of coteries has made it clear that a coteri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individual parts: it is a set of relations. In this respect, a coterie is a form of network as defined by sociologists; I have also benefitted, therefore, from the contributions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generalizing the structures of networks and in defining terms for their description and study. While I have chosen not to attempt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any of the groups I will be examining,35 I will draw on several of these key concepts and terms in the chapters to follow – in particular, the notions of network density and multiplexity of ties between members; of the individual motivations that might influence the relative density or openness of a particular network; of the varying roles played by individuals or “nodes” in a network as a function of their relations with other members; and of the significance of members of networks who serve as “bridges” or “brokers” – individuals such as Thomas Birch and Elizabeth Carter, for example –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manuscript materials, and new ideas across “structural holes” between groups. Bruno Latourrsquo;s insistence, in what he calls Actor Network Theory, that the social is continually created and recreated by the very transactions that forge it and that non-human agents are “actors” in such shifting constructions, has influenced my emphasis on the unique and continually reconfiguring characters of different coteries and on the function of places, genres, and tropes, as well as key human actors, in the story I am telling. In general, however, I will be assuming that social conditions external to any particular network – for example, stereotypes about country versus city life, codes invoked in communications between members of different status groups, or the rules known to govern manuscript exchange between members of any coterie – create a climate of expectation within that network. What becomes interesting in this light is how an individual group might negotiate and refine those expectations, or reject them altogether.36
The plan of the book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ive decades of 1740–90, from the formation of the coterie centered at the estate of Wrest Park upon the marriage of Philip Yorke and Jemima Campbell in 1740, to the transmediation of coterie travel writing into the printed domestic tour guide in the 1780s (with a follow-through beyond 1790 in the case of the afterlife of William Shenstone). Its overall arc is thus roughly chronological, moving from the casual interpenetration of manuscript- and print-based cultures characteristic of the small, London-centered literary world of the 1740s to a more institutionalized, complex, and geographically extensive print system with which various elements of coterie practice coexisted in various states of equilibrium in the latter decades of the century. At first glance, this broad change might suggest that coterie culture moves from a position of superior cultural authority to a state of embattlement and decline. In the f
全文共24112字,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爱和爱泽尔更仔细地观察文学和出版的价值观和机制,注意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转录习惯,一种相对非正式的风格和坦率的风格,一种“混合的喜悦”,以及一般的不关心区分个人作者对作品做出了贡献或准确地归纳了作品.33 Arthur Marotti,“手稿”,“印刷”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抒情作品”(1995),更详细地讨论了文学作者的作品和与发展媒介区分开来的作品的印刷 - 诸如对组合过程的开放,非个人主义的理解的特征;这种组合物的社会嵌入或“偶尔”性质;由社会背景(例如,诸如法院旅馆的起源地)创造的团结,而不是风格或技能的一致性;以及某些形式的相关流行,如答案,模仿,墓志铭和表情,以及潜在的冒犯性主题。 1625年至1725年,英国社会批评中的保罗·特兰兰德和泽恩·特格格(Zeynep Tenger)更注意了对于作品的文学批评实践,其特征是以一种共同的“修正”方式来改进作品,批评是一种表达社会义务,文化活动功能在内部“创造和建设社会债券”,从而通过建立社会,政治和文化声望为整个群体服务“。34
这个关于苗圃结构和实践的历史性工作已经很清楚,一个小圈子不仅仅是个别部分的总和,它是一套关系。在这方面,小圈子是由社会学家定义的网络形式;因此,我也受益于社会网络分析在推广网络结构和界定其描述和研究方面的贡献。虽然我选择不尝试对我将要研究的任何组织进行定量分析,但我将在以下章节中介绍几个这些关键概念和术语,特别是网络密度和关系的多重性会员可能影响特定网络的相对密度或开放性的个人动机;个人或“节点”在网络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作为其与其他成员的关系的函数;以及作为“桥梁”或“经纪人”的网络成员的意义 - 例如Thomas Birch和Elizabeth Carter等个人在传播信息,手稿材料和跨群体之间的“结构性洞”的新想法。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他所谓的“网络理论”中坚持认为,这种社会不断创造和重建,这种交易是伪造的,而非人类的代理人是这种转型结构中的“演员”,影响了我对独特和在我讲的这个故事中,不断地重新配置不同的小组的人物,以及地方,流派和热带的功能以及关键人物。然而,总的来说,我将假设任何特定网络的外部社会条件 - 例如,关于国家与城市生活的定型观念,不同地位组织成员之间的通信中引用的代码,或者管理委员会成员之间手稿交换的规则任何小圈子 - 在该网络中创造一种期待的气氛。有趣的是,个别团体如何协商和改善这些期望,或者完全拒绝他们
这项研究着重于1740-90年的五十年,从1740年菲利普·约克和詹姆马·坎贝尔结婚以来,组建了以Wrest Park庄园为中心的小圈子,将小圈子旅行写作转化为印刷的国内导游在1780年代(威廉·沉斯斯通的来世),超过1790年的追随者)。因此,其整体弧度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从17世纪40年代以伦敦为中心的小型文学世界的手稿和印刷为基础的文化的偶然渗透转变为更制度化,复杂和地理上广泛的印刷系统,其中各种元素小圈子实践在本世纪后半叶处于不同的均衡状态。乍看之下,这种广泛的变化可能表明,小圈子文化从优越的文化权威的位置转移到一个安置和下降的状态。在本书涵盖的最后十几年中,小圈子的社交性及其实践使得作为表现形式的复制对象的表现出现在表现中,通常作为无效但威胁性的现象与印刷媒体系统区分开来,与此类似,在这种情况下弗朗西斯·伯尼(Frances Burney)的剧本“威廉王国”(The Witlings),于1779年组成,而博斯威尔则对撒母耳·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李登堡之王”的争吵进行了讨论。然而,脚本的这种封锁掩盖了其持续关系的亲密关系,以印刷为媒介“其他”。我们也看到小圈子作为修辞战略的代表,授权一些印刷品最“向上移动”的形式,如托马斯·西的1778年“湖泊指南”:致力于景观研究的恋人,以及所有访问过的人,或打算访问坎伯兰湖,威斯特摩兰和兰开夏郡的湖泊,并引用了传统的绅士交流旅行帐号。而我的最后一章将会追溯到17世纪40年代至17世纪90年代,文学圈子对诗歌混乱的编纂者的一致呼吁,即使他们越来越多地从事杂志和选集的材料。因此,我将介绍的叙述是不是衰落的,而是在小圈子和商业印刷业之间不断改变地方平衡。我会研究合作,相互剥削和偶尔的紧张局势的情况,分析这些事件揭示了关于十八世纪媒体生态学和转移和调整的风险。
第一章概述了两个互相渗透的小屋。一个,纽约 - 灰色小圈子围绕新近结婚的菲利普·约克(Philip Yorke),大臣大臣的长子和未来的第二个伯爵Hardwicke,以及位于Wrest的地理中心的吉米玛·坎贝尔(Jemima Campbell)最初似乎朝向过去,社会精英和客户偶尔交换诗歌,发挥机智戏剧,进行赞助工作,影响舆论,寻找地点或生活。另一方面,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苏珊娜·高尔莫(Susanna Highmore),托马斯·爱德华兹(Thomas Edwards)和赫斯特·穆尔索(Hester Mulso)在17世纪初期出现了相反的情况 - 从根本上讲,然而,我的分析不仅将显示每个人如何按照既定的文派交流规则进行活动,而且还将显示每个群体的特征如何从其历史情况和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中脱颖而出。
因此,17世纪40年代的约克灰色小圈子同时代代表着文化文化在几个方面的潜力:在其早熟的,道德上严肃的人才中,首先以机密出版“雅典文字”和“国家的政治和文学前途;在中国人才中心参与的比赛中,如马尔戈里斯·格雷和凯瑟琳·塔尔博特;并在菲利普·约克(Thomas York)与托马斯·比奇(Thomas Birch)之间形成的跨媒体联盟,他们共同在国家手稿保存和访问实践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大英博物馆的成立。理查德森小圈子,虽然在社会和政治上较少预先接触,不仅在相互意识和尊重,而且特别是Talbot和爱德华兹这两个人的成员中,与约克 - 格雷小圈子接触。这些交叉点本身就表明了17世纪40年代和1750年代的社会和媒体流动性,当一个自制打印机可以追求社会上的小圈子的乐趣,因为他在小说中代表他们,精英小圈子的成员可以找出认识一位小说家,他们希望通过印刷获得社会贡献。然而,理查德森小圈子,特别是撰文人和年轻的苏珊娜·高莫尔和赫斯特·穆尔索之间的年龄和性别不平等似乎造成了一种不平衡,导致了17世纪50年代中期的解体。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将提供证据,证明年轻的诗人和小说主义者穆尔索(Mulso)通过这个小圈子的文化影响而取得的令人惊奇的成就。
我的第二章追溯了17世纪50年代伊丽莎白·卡特和伊丽莎白·罗宾逊·蒙塔古(Elizabeth Robinson Montagu)的进步,形成了一个新的混合性别的小圈子,它在17世纪50年代末期融合了伊丽莎白·蒙塔古和乔治·里特尔顿爵士的中心人物。尽管蒙塔古与波特兰公爵夫人的联系有所减弱,以及卡特尝试推销塞缪尔·约翰逊漫步者期刊的失败,但我建议这两位女性成功寻找一个将社会性与影响力和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圈子 - 特别是文学 - 刺激。 Montagu的自我完善计划通过友谊和卡特的钦佩和财务奖励的所有作品的Epictetus的订阅出版物带来了他们在一起1758年,在蒙塔古赢得了对李特尔顿的钦佩,几年前,与威廉·普列内巴斯阁完成了内圈。我特别参加了这个小圈子的两个最富有成果的时期:1758 - 62年的早期和1769-73年的后期,终止了李特尔顿的死亡.37回顾了这个小圈子所做的文学作品的模式,特别是这本熟悉的信和偶尔的诗,本章详细介绍了该团队为自己的项目以及诸如Hester Mulso Chapone等保护组织的战略部署。因此,我从1761年的wid夫时期回到了查波姆的文学生活,阐明了优越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与道德监督的良好平衡,使得沙波在这个小圈子的赞助下茁壮成长,使蒙塔古独特地适合作为赞助人和煽动者她的客户成功地转移到印刷作者身份。尽管Montagu-Lyttelton小圈子作为一个平台,作为打印作品的平台,凯瑟琳·塔尔博特(Catherine Talbot)尽管与卡特的密切友谊以及她作为打印计划推动者的角色,仍然远离了这个小圈子。本章最后讨论了塔尔博特避免充分参与,即使是在小圈子文学交流中,因为它可能会产生超额的名气。
从个人而不是集体的角度来看,本世纪中叶几十年来印刷和剧本媒体系统的界面,以第三章为出发点,构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未婚未成年人生活的无益在十八世纪中叶受过教育的女高音女子或男子手段有限。虽然小圈子的生活有一些理由被描绘为社会精英内容的手段,通过相互加强和限制访问来保护其文化威信,我展示了爱德华兹,塔尔博特,卡特和查普罗如何表达了类似的存在危机。对于这样的个人,参与小圈子生活可以提供文化影响力,从而有意义的存在感。在卡特和查波蒙的案例中,这个效果在Montagu-Lyttelton小圈子主持下的印刷出版物的故事中得到最充分的实现。然而,本章的重点是隐士诗人威廉·申斯通(William Shenstone)的职业生涯。像Edwards这样的领导者,通过复杂的环境,过着农村退休生活,Shenstone不仅建立了诗集交流的文学小圈子,而且围绕Leasowes围绕着多媒体艺术实践,发展成为着名的“fermeorneacute;e”。 “神玄主义者,神石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无所事事“和经济限制转化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以小圈子为基础的关系价值体系,体现了谦虚的规模和简单性的味道。这个悖论进一步发挥自己在神石的小圈子的声誉的媒体史上:在通过Leasowes流传的游客和他的诗歌的手稿流通中获得了相当的认可,他最终获得了更广泛和更民主的广泛的声望创新书商罗伯特·多德斯利(Robert Dodsley)的帮助,罗伯特·多斯利(Robert Dodsley)在他自己的手稿和他的小圈子的诗歌中大量创作了他的着名“诗集”第四卷和第五卷
事实上,神石的诗意人物和美学价值观在1763年去世后才延续了数十年,从多德斯利出版他的两卷作品“威廉·沉斯斯通”散文作品Esq。在1764年,随后在1769年第三卷的信件。威廉·沉斯斯通的来世 - 他的诗和散文的多个版本,零售的轶事他的生活和他的花园在流行杂志的描述,致敬诗和模仿,而他和十九世纪持续良好的传道者的形象交易也是第四章的主题。但是这个来世不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上,Dodsley的作品版可以看作是引起分歧的接待历史。一方面,关于(或更准确地说,批评性解雇)神石的文学批评性评论倾向于一个多世纪以来跟随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的领导,尤其是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强调了达斯利传记序言中提到的不满和不满,画出一个永远不快乐而又虔诚的隐居者的高傲的照片,他那一天的更艺术诗歌和艳丽的景观花园的朦胧反思只是文学史上的脚注。
然而,通过最近的数据库产品提供的出版和期刊档案的回顾显示了第二个被遮蔽的接待传统本身是双重的。在一个线索中,我们发现神石的小朋友作家,其忠实的朋友,特别是理查德·格雷夫斯,继续在多德斯利公司发表的许多出版物中表达他们的尊重他的个人素质,作为仁慈的导师以及他的艺术成就。这些“高”文学作品 - 地形和道德诗,精神吉诃德和专题小说,以及回忆录 - 与神石的渗透和他的声望并入到大西洋世界各地的各种期刊,通常是通过调解多德斯利版。那最后一个“神石”对于事实来说常常并不准确,而是约翰逊由Duns追求的园丁本身值得关注。我对William Shenstone的接待研究,不仅提出了专业文学评论家作为印刷机构的日益增长的摇摆,而且还将Shenstone的少量小圈子的生活作为多年来管理的杂志进行零售,以抵制屈服于这一权力 - 因为它代表了他的同时代人和直接的继承人是他们渴望的理想,通过将民主化的品味概念应用于生活中最平凡的方面而赋予了意义和乐趣。以这种方式,社交文学小圈子及其价值观被转化为一个虚构的,虚构的“神士人”社区。
从本世纪后半叶的媒体主张权威的起点再次开始,我开始了第五章与伊丽莎白·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的命运,以及17世纪70年代和1780年代乔治·李特顿(George Lyttelton)逝世以及17世纪80年代的圈子他们亲密的小圈子的灭亡。回顾Montagu及其女性朋友越来越多的公众代表是“Bluestockings”,我认为,默认从与小圈子网络的个人关系离婚的印刷品名声,Montagu自己容易受到对小圈子做法的种种攻击和这个时候在某些地方出现的人物。对于这种脆弱性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专业的“男性”作者与女性化的小圈子业余者之间发展的话语二分法,另一方面是强生和蒙塔古隐含的二分法,因为前者将自己置于关系到后者。随着蒙塔古和盟友如现在哈德维克哈德维奇的诸多菲利克·约克的抵抗力越来越大,打印了生活中受到重大影响的人物的“人物” - 哈德维克爵士,巴斯爵士和乔治·莱特顿爵士 - 的舞台是基于相反的媒体文化和各自的宣传观点而设立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将约翰逊和蒙塔古之间的争吵放在了前1781年的“利特尔顿生活”之间的争吵中,我表明,这个争吵不仅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集团对一个庄严的约翰逊的“微弱的尖锐的抗议”,就像博斯韦尔所说的那样,但是而是声称作者的品格与他的作品一起要求进行公开批评的人之间的对峙,而那些感到男人声誉的人是他个人圈子的财产,被捍卫,并且不受利润饥饿的书商的束缚。在这方面,第5章重新审视和重新阐释了神石的朋友理查德·格雷夫斯(蒙塔古的鼓励)的姿态,把小圈子成员的第一手经验的权威与他在“沉思的回忆录”中的城市印刷作者的狭隘观点相抵触, 。
然而,如果第5章讲述了分化和不和谐的故事,第6章将通过探索一个相反的情景来挑战这种叙事的概括,这种对立的情景是通过前几章所涵盖的五十年的共生和相互加强之一。通过Philip Yorke,Jemima Gray,Elizabeth Montagu和George Lyttelton的手稿旅行写作的讨论,我通过商业导向的印刷品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追溯了国内旅游叙事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休闲绅士生产和流通的手稿和手稿。从1742年第三版的丹尼尔·迪福巡回演唱“英国的整个岛屿”开始,这种印刷形式在本世纪以来呈现向上的增长态势,逐渐增加了人们的尊重,因为进取的编辑们征服了旅行绅士的权利,对国家最遥远的角落越来越感兴趣。这种欣赏本身就成为诸如
全文共7165字,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145053],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