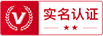社区治理:转型、演进、争辩与发展文献综述
2020-04-01 11:04:56
改革开放简而言之可以说是政府还权于民的一个过程,随着”大维稳体制”与行政主导体制弊端的不断显现,”社会管理创新”势在必行,成为继续改革开放的着力点,使得有关社区治理的研究方兴未艾。
”社区”一词最初来源于社会学家滕尼斯的著作,腾氏认为社区与社会是两种不同的人类群体,社区应当是建立在血缘、地域、情感和自然意志上,富有人情味和认同感的社会共同体。之后的美国功能学派教授帕克也认为”根据区位组织起来的社会 (在地域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 )就成了一个社区 ( community), 而不止是一个社会 ( society)”。[1] ( P55) 在治理理论的话语体系下,社区治理成为社会建设的一部分,在这里,社区与社会并没有进行类似腾氏那样严格的区分,学者普遍认为”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在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2]
国内学者对社区治理的定义可以说是大同小异。魏娜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一文中认为”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3]许硕也在《浅谈社区治理之路》一文中认为:”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4]杨云燕在《浅谈社区治理》中指出社区治理的实质是”社会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构建过程,是政府与社会分权的过程,是公民社会发育的过程,是民主完善的过程。”[5]
我国学者针对社区治理从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多种学科角度进行了大范围深入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方社会建设理论、模式的演进之路有何借鉴意义?
刘少杰、王建民在《现代社会的建构与反思#8212;#8212;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来龙去脉》疑问中就社会学理论作为社会建设理论这一事实而言,将西方传统社会建设理论分为科学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在论述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当代形态时,又举例介绍了理性疯癫论、风险社会论、生成结构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后现代性社会建设理论,并从中
归纳出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内在理路,即从面向物的社会到面向人的社会,从结构主义到建构主义,从建构性到反思性,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到全球化的视角。[1] 唐铁汉、李军鹏在《西方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及其演变新视野》一文中从宏观上将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发展历程分成产生、发展与反思三个大的阶段,并在三大阶段之下又做了更进一步的划分:社会秩序理论与社会改良理论,福利国家理论与福利社会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与”第三条道路”理论。[2]潘西华在《当代国外学者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研究综述》一文在前述两篇论文的基础上”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批判主义的社会建设思想为考察点,详细论述了反应社会建设这一过程的社会治理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社会风险理论、社会公正理论、社会福利理论等诸多理论分流。[3] 而唐元松在《论西方国家社会管理的演进与启示》一文中以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人均GDP的阶段性增长为划分点,将西方国家社会管理演进之路分为:1、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管理,2、混合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管理,3、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管理。辨析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成果的成败得失之后,又论述了五点获得的启示:(一)社会运行管理机制须根据形势发展适时进行调节改善;(二)公共服务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机制;(三)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能泛市场化;(四)社会政策要着眼于效率与公平并重;(五)社会管理逐渐从统治走向善治。[4] 郑杭生在《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参照系及其启示#8212;#8212;一种中西比较的视角》一文中认为中西方国家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又不能对西方的经验照抄照搬,从中西方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特殊性出发,论述了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和欧洲的福利主义模式现存的危机和与中国国情的不适,告诫我们”借鉴国外,跳出国外”即一方面必须学习和借鉴国外,,因为不学习和借鉴西方,就会脱离人类文明大道,就不可能高质量地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另一方面又必须跳出西方的理论框架,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5]
二、社区治理转型中的问题
当下学者研究的”社区治理”理论无疑是从西方引进的新名词新思想。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保甲制”等类似的社会管理制度,但从统治与治理的二分理论上可以看出二者的明显不同。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由”单位制”也因为不适合改革开放的新形式而被削弱,代之以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并逐渐想自治型治理模式转变。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一个主导者变成合作者继而成为监督者、指导者,这是当下中国社区治理可见的路径。
对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原因,张小劲、于晓虹在《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宏观框架的考察与比较》一文中有精辟的论述:”相对而言,外部事件主要起到了”警报#8217;作用,中央最高领导人由此意识到整体的国际环境不仅可能会发生巨大的转变,而且会引发主要城市国内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连锁响应;内部事件的出现才真正改变了整体的政策思维,更确切地说,2010年以来国内群体性事件的急剧上升,突显了所谓”大维稳体制#8217;的困境和政府行政主导性体制的困境。”[6] 程亮在《社会转型中社区治理的发展历程与困境》一文中总结了较早时期(05年之前)社区自治中的五点困境: 1.权利有限、经济匮乏。2.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薄。3.社区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7]连玉明则在新近发表的《关于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指出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稳定风险。由于这些风险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一旦爆发,很可能导致非常态扩散和放大。并列举了五种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的不稳定因素:1、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超过0.5,逼近社会容忍线;2、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并有激化的趋势,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现象乃当前之首;3、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4、仇富、仇官、仇权的社会心态问题日渐突出,极易借助现代传播媒介迅速放大为社会危机;5、非传统安全危机正成为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胁。之后又提出了当前的社会体制改革存在五个方面的缺失:一是中产阶级的缺失;二是社会的缺失;三是制度的缺失;四是信仰的缺失;五是权威的缺失。[8]郑杭生在《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区建设#8212;#8212;对社区建设的一种社会学分析》一文中指出在我国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过程中有些地方社区组织行政化的倾向仍然严重存在, 有的甚至还在发展,并做了详细说明。[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