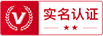汉正街淮盐巷片区复兴研究---吴家正巷复兴规划与建筑设计毕业论文
2021-03-13 23:44:33
建筑新老价值的共存
由Ilze Paklone 采访
你是怎么去辨识自己的作品?你工作中重要的是什么并且是什么因素最影响它?
我一直很喜欢重建。我记得当时我在我工作室时我熟悉于建筑记录的问题,善于处理重建的主题并沉迷于此。我的毕业设计项目和里加的历史中心的城市街区的介入重建有关。展现我们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奠定了我全部的工作。一个建筑师对于历史物质和它的改变的很小心的态度,在遗产和现代干涉之间找到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工作总开始于对一个地方的历史谨小慎微的调研,了解历史层面结构的真实性。
我可以说拉脱维亚是个非常纯正,未受破坏和令人惊奇的平衡的地方。当我们快速的并且激进的改变环境的时候,建筑的活动可能会变得很危险。因此我感觉想要理解内容、组织结构、空间联系和与之有关的元素的范围及使之有最终的合理性成为了我们作品中重要的一方面。环境也说明很好的设计会服务于项目。设计的合理性对拉脱维亚总是很特别的。我从这个项目的合理性里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语境主义者。在我看来,语境主义者给我了机会让我们的设计不再是简单的好项目而更多的是从他们存在的物理环境中并通过解释或者革新来获得他们的价值。环境设计一个有价值的方面就是他不是很干涉已存在的现实。它超越了它,因此它具有潜力成为永恒的价值。这种设计不在感觉中自私它不需求任何花销的关注。而很重要的是,设计几乎无停顿的混合于环境中作为它不言而喻的一部分并且最重要的是创造出围绕它的有着特别价值的环境。虽然外部形式有关联,但我们更倾向于从环境、项目、利用性和价值的内部关联中创造诗意的意向。
就感觉现在是照顾老建筑合适的时机。“照顾”形容我重建、革新和复原工作最好的词,我的创造性能在新旧建立联系间表现它自己。充满想象力的时刻即使在旧建筑技术革新的时候也能发现。很高兴能感受到一些旧的形式在一种新的水平但技术和建筑的干涉几乎不可见。这是个解决西欧的物质遗产很特别的机会。这包括拉脱维亚。
如果我们领会到建筑专业的关系,我们能概括出拉脱维亚建筑纪律的变化和我们自己实践的三个主要方向。第一,新的建筑实践,包括我们自己的,是独立和相等专业的集合不包括那种可以作为标志的大师作品的建筑。关系更加水平。同样组织工作的过程和最终成果。即使在公司的名字上它也表明它自己。很少有以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第二,年轻一代对周围的进程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和意识。这在理解动作和项目内容如何影响边缘环境上有所证明。它是一个人自己的影响和关联的综合体现。第三,交流的模式改变了。通过建筑方式交流重要的社会和文化表现的方面使我们在项目中研究的。以装饰的方式展现建筑是很多参加者涉及到的而不是作为一个不综合的纪律仅仅对于很少的人。专业性拓展了它的界限:理解建筑不仅仅是物理建筑,也关于理论、社会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流。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有两个工作室。DJ建筑处理理论研究和利益,小范围的项目,透视和安装和环境项目。另外一个,MAAS,处理相对大些的建筑项目并关注比赛的参与者。我在OMA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的工作室让我对把建筑当做研究,视觉和叙事来思考印象深刻。我感兴趣的一个特例在于挖掘出把透视法当做潜在的设计独特的空间位置。毁掉理解和纪律的界限是个很特别的感觉。比如,我们曾经在城市环境中永存—固态的建筑,固定的街道。透视元素有潜力能让我们以惊奇的方式看到平凡的城市。
你能形容下设计的背景环境吗?就在拉脱维亚刚刚与1991年重新获得它的独立的时候。并且这个处境在过去的25年间是如何进化的呢?那个时候的优先权是什么?现在这个时候的优先权又是什么呢?你如何认为在这25年间,拉脱维亚的建筑已经加速了?
这25年来我对于我工作的态度和我在重建上的关注从没有改变。尽管建造的压力更快更廉价,我一直做着我认为重要的—对于调整环境到现代的明智的态度。我确实没有野心去建造那种很显眼的东西。历史物质和他的变化间的微妙的对话,你怎么改变他们让他们以一种新的方式表现对我来说更重要。这个立场可以在我位于Kipsala的木质收藏品中所见。
当然啦,世界改变啦。我感到现在有更多人关注遗产了。这也可以在上次威尼斯双年展上体现出来,这是一个整体的趋势了,不是炫耀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不是有形的可见的。遗产工作给予了拉脱维亚的建筑地形一个开端。
如果我们特别的思考过去25年的进化。它更加是持续的思考一个同样的主题和内容一遍又一遍而不是一个想法跳跃的改变。
这个工作室是建立在我们重新获得独立之前一点点的。原则上来说,启蒙和工作室的进化与很多进程相关联,这个进程又与养育出新的处境有关。再从原则上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东西都已经改变了。一直到独立,很多城市中大范围的重要的建筑物不再被人们继续开发。在25年之后,我们不再和这个时间剩余的人所隔离,不再像我们之前那样了,因此新的设计在当地的文化环境中不再是传统的巨作了。在这个时刻,整合与合作,谨慎的材料的工作室,持续性的各种问题来到了最显眼的地方并且变成了更大的挑战而不是制造出新的惊喜。在25年前,设计更倾向于的是去探索未知和实验未知的土地,那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现在都改变了很多很多。人们对于历史价值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让更多的空间能让新和旧的价值共存起来。现在不再有严格的武断的方法。现在社会有一个机遇能让人们去讨论建筑建造物的价值,让人们去评估他们。
所有的在文化进程中的实际情况都反映出某种异常行为和一种在建筑中被设计为所要求的需求的一种延期,从头到尾,制定和实施。对于人们来说,在某件事情正在发生的一个确切的时刻急忙去了解,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这些结果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可以一直是综合的。人们对于周围环境的意识认知开始向合理性那方面延伸—更少的去讲排场并且更多的表现对事物本质的赞赏和理解。这种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建筑来说,并且它作为我们的任务之一,让我们去集中注意力去理解真正的需求而不是不合理的愿景。
也许,现在就是那些更小一点的项目能有更高的建筑质量的时机了。
有很多很多的疑惑都在1990年代被呈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飞到了一个未知的领域并且是一种尝试去迅速和专业地去应对改变。虽然历史性上来说,我们已经成为了西方的欧洲的文化空间的一部分,在我们重新获得独立以后,这里有一个明确的欲望和矢量去强调它。我们位于西方的欧洲的文化的地方是一个很有趣的充满历史性的结果,同时也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项目的背景中—里加城堡的重建复兴。西部的欧洲的文化空间的启蒙开始于十字军战士们,这些十字军早在10世纪的时候就到达了这片土地,并且他们试图去镇压当地的异教徒们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对于西部的欧洲的文化的爱好成为了现实,虽然我们变成了相对来说也更贴近于斯拉夫的文化。
我们理想化了那些我们认为是落后的东西,比如说铁幕,这种东西是在苏工代表会议联盟和西方世界富有想象力的一部分。我们倾向于去思考西方世界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美丽的一种事物。在这25年间我们已经稳固下来,并且有能力去产生我们自己的理解和美。
在人们获得独立之后,出现了一丝不同,那就是旅行并观看那些只能从文献材料中了解的建筑,去看那些积极的一面同样也去看它的消极的一面。这些都花费了我一些时间去透彻理解它们,并把它们吸收进我们自己的思考中。反过来看,那些年轻的一代们,他们就不存在这些界限的限制,他们已经在我们现在这种地方并且没有履行任务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