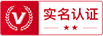被遗忘权的本土化建构与法律适用文献综述
2020-04-29 19:57:53
一、研究背景
互联网时代,人们在享受科技信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恐惧的发现#8212;#8212;社交平台、搜索引擎、手机应用软件等已经随时掌控你的信息,追踪你的行迹,推送你的喜好。当你要抹去”被记忆的数据”时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财力。在当今社会,互联网像一个巨大永久的记忆库,收集着所有信息,包括各种隐私内容,这使得我们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呈现出”裸奔”的状态。大数据背景下的搜索引擎能力和强大的服务器功能使得我们想要行使删除行为成为天方夜谭。基于上述的现实状况,被遗忘权诞生了,这既是大数据时代信息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法律对于大数据运作的规范与控制的最佳路径。被遗忘权来源于欧盟法律的规定,主要相关法律文件:1995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2012年《统一数据保护条例建议案》以及2016年《个人数据保护条例》。被遗忘权首次出现在2012年《统一数据保护条例建议案》,后经过审阅和修改,于2016年《统一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规定了被遗忘权。2014年谷歌诉冈萨雷斯案以司法判决的形式确立了被遗忘权。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尚未出台,已经制定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散落于一些法律法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规章中,缺乏体系性,这使得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任务尤为艰巨。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相较国外而言,国内对被遗忘权的研究起步稍晚,被遗忘权的保护范围与个人数据有关,以往学者研究个人数据都着眼于个人信息权利、隐私权的视域。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些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已经无法涵盖被遗忘权的内容。
1.关于被遗忘权的定义或内涵我国学界关于被遗忘权的定义还没有形成统一界定,有学者从被遗忘权的性质进行界定,如陈昶屹主张被遗忘权是一种删除个人数据的权利(陈昶屹,2014)。还有学者从权利保护的对象给被遗忘权下定义(吴飞、傅正科,2015)。综合这两种定义角度,都缺乏确切的尺度,逻辑上容易造成混乱。
2.被遗忘权的权利性质关于被遗忘权的性质,主要有隐私权权能说、个人信息权能说、独立人格说三种。(1)隐私权权能说。此观点主张被遗忘权是隐私权的扩展,例如:赵锐认为被遗忘权是隐私权在互联网时代的深入和拓展(赵锐,2016)。张建文基于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和被遗忘权的关系,认为被遗忘权是在隐私权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的新的内容和范围(张建文,2017)。(2)个人信息权能说。提出此理论的学者根据《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认为隐私权无法保护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而应当由个人信息权加以控制。杨立新、韩煦主张从理论上,应当将被遗忘权认定为个人信息权(杨立新、韩煦,2015)。但是考虑到现实情况,提出暂时归为隐私权范围,受《侵权责任法》保护。梁辰曦、董天策认为被遗忘权的内涵与个人信息权更为接近,体现的是个人对已公开的自己的信息的更新、删除、了解用途或去向的控制权(梁辰曦、董天策,2015)。张里安、韩旭至认为被遗忘权脱胎于个人信息自决权、是其原有权能遗忘权与删除权在大数据时代下的组合升级(张里安、韩旭至,2017)。(3)独立人权说。独立人格说的学者大多从被遗忘权的起源着手,认为被遗忘权是新型人格权。如廖磊提及被遗忘权的价值在于保护信息主体不受过时个人信息的羁绊,其核心在于遗忘,删除只是手段,因此被遗忘权是一种新型人格权(廖磊,2017)。 梅夏英提出被遗忘权应当有独立权能”被遗忘权不属于隐私权或个人信息权的范畴,它是公共利益和个人法益的混合体”(梅夏英,2017)。
3.被遗忘权的具体内容
(1)权利主体现有的文献都普遍认为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是自然人,需要思考是否将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进行类型化分析,如对公众人物的被遗忘权是否应当有所限制?法人和其他组织是否能够基于在网络上遗留下的数据成为大数据利用的重要资源这一理由而被赋予被遗忘权?上述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有所涉及,但挖掘深度不足,仍需深入探讨。
(2)权利客体关于被遗忘权的客体,目前争议较大,第一种观点认为是针对”不当的、不相关的、过时的信息”。第二种观点认为是针对”不恰当的、过时的、会导致信息主体社会评价降低的信息”。事实上依照2016年《统一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来看,第一种观点表述并不准确。需要结合外国立法理论做进一步的研究。
(3)义务主体现今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被界定为信息控制者或数据控制者,这一做法与欧盟一致。但是数据控制者履行删除义务的情况不尽相同,应准确厘清义务主体的范围为确定侵犯被遗忘权的侵权责任主体的范围做铺垫。